【欧洲时报汤林石编译】在萨曼莎·埃利斯的母语中,人们用“在心上切洋葱”来表达“在伤口上撒盐”的意思。当她意识到自己的母语正在“死去”时,她决定造一艘“方舟”。
在《帕丁顿熊》系列电影中,我们看到一只来自秘鲁的小熊到伦敦后在陌生文化中寻求“归属感”的历程。萨曼莎·埃利斯参与了《帕丁顿熊》前两部的制作。影片中,橘子酱三明治是帕丁顿熊与故乡的情感纽带;银幕之外,身为移民后裔的埃利斯也在努力保留和传承着属于她的“橘子酱三明治”。
在埃利斯的新书《心上切洋葱》中,她讲述了作为伊拉克犹太移民后代的个人经历,探讨了文化的留存与消逝,尤其是她那濒临失传的母语——犹太伊拉克阿拉伯语。
早在公元前597年,犹太人就开始在伊拉克定居。那时还不叫伊拉克,而是叫巴比伦。当时,新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占领了耶路撒冷,犹太国王被俘,大批犹太人被强制迁往巴比伦,作为劳工去挖掘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运河。
这些犹太人原本讲希伯来语,但到了巴比伦后很快转用当地语言——阿拉姆语,发展出一种叫“犹太巴比伦阿拉姆语”的变体。公元前539年,波斯人征服巴比伦之后,这种语言又被波斯语影响。等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横扫中东时,犹太人也像其他人一样改讲阿拉伯语,但他们的阿拉伯语始终带着阿拉姆语和希伯来语的痕迹。
20世纪40年代,伊拉克有15万名犹太人。1950到1951年,大多数伊拉克犹太人迁往以色列,埃利斯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。她完全不知道父亲小时候长什么样子——他没有留下任何10岁以前的照片,因为在1951年离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时,每个犹太人只被允许携带一个小手提箱,其余资产均被没收。
埃利斯的母亲直到1971年才离开巴格达,搬到伦敦。在这里,她的父母相识了。“我的父母是在犹太伊拉克阿拉伯语中相爱的,但他们并没有教我和哥哥这门语言。”
“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当年建议他们‘只说英语以免让孩子产生混淆’的社工,但其实我的父母自己也觉得,教一种注定要消失的语言毫无意义。”埃利斯在书中写道。1975年,当她出生时,伊拉克只剩下大约400名犹太人了。
埃利斯的父母坚持用英语和她说话,给她念英文书籍。“但所有八卦、所有轶事、所有神秘而令人兴奋的‘大人世界’都是用犹太伊拉克阿拉伯语讲的。”埃利斯觉得不甘心,想自学这门语言,于是她努力倾听、问了很多问题。“大概9岁的时候,我突然全明白了。就像穿墙而过,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那些词都属于我了。”
起初,她没告诉任何人,偷偷地听父母讲话。“直到有一天,我爸说了个笑话,我笑出了声,才被发现。”从那以后,这也成了父母和她之间的“加密语言”——在伦敦,会讲这种话的人已经寥寥无几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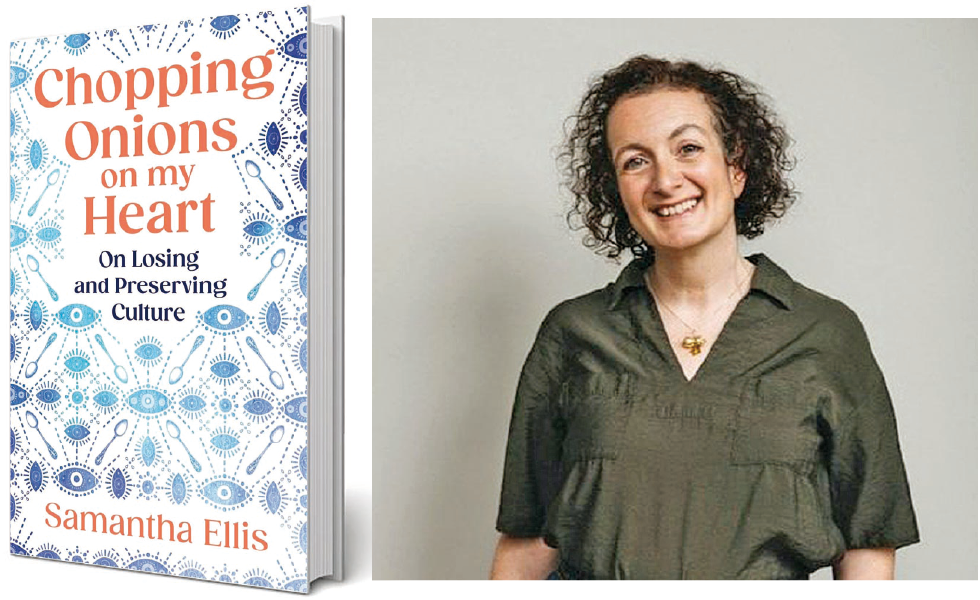
左图为《心上切洋葱》,右图为本书作者萨曼莎·埃利斯。(图片来源:企鹅出版社/作者官网)
2019年秋天,埃利斯带着两岁半的儿子在伦敦的一个游乐场里玩耍,遇到一个会说法语的小男孩。在和男孩的妈妈攀谈时,她得知男孩上的是附近的法语幼儿园。埃利斯说,自己原本也想让儿子去那家幼儿园,从小掌握两种语言。男孩的妈妈有些疑惑地问:“可你不是法国人呀?为什么不送他去讲你的语言的幼儿园?”
埃利斯突然一阵悲从中来,回答道:“我不能。我的语言已经死了。”
准确地说,是“正在死去”。2019年,伊拉克仅剩5个犹太人。新冠疫情带走了其中2人,现在只剩3人。埃利斯感到内疚:“这语言之所以正在死去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没有尽全力去传承它。”想到再过不久,这些话就会从人间彻底消失,她感到一阵绝望。
她打开电脑,开始查询犹太伊拉克阿拉伯语的现状。起初,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地图上翻遍了伊拉克的语言,却找不到它的踪影,最后才发现它出现在以色列——因为如今大部分使用者生活在以色列。“但从情感上讲,把我的语言标注在以色列而不是伊拉克,总觉得错了。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它是‘语言’,而不是‘方言’。”
埃利斯决定行动起来。她打算编一本词典,但意识到“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字母系统”,这种语言几乎从未被系统记录过,有时用希伯来字母书写,有时用阿拉伯字母书写。伊拉克犹太作家们通常选择流亡后定居国家的语言来写作——多半是希伯来语,也有英语和法语,因此“没有人会为了文学价值来拯救我的语言”。
但埃利斯并不认同“只有有用的语言才值得留存”的想法。疫情期间的某个深夜,埃利斯读到一项来自加拿大的研究,发现学习本族语言的原住民青年自杀率显著降低。研究者认为,学习祖先的语言,会让我们更加有归属感、更具韧性、精神更强健、心灵更富足。这加深了她保护母语的决心。她开始记录日常用语,采访家人、语言学家,和儿子说母语,学习制作故乡的美食……用她的话说,就是在洪水逼近时造一艘“方舟”。
《卫报》书评指出:“她用食物、艺术、歌曲,尤其是语言作为载体,回望自己那濒临消失的文化,最终领悟到:身份的转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,它也可以是一种拓展与演变。”
(编辑:唐快哉)
